作者:夏辉
公司重整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于债务人借助破产法提供的谈判机制与债权人就当前的债权契约重新谈判,无力偿债的公司债务人得以避免清算,债权人整体上又可以得到大于清算所能得到的支付,实现双赢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1】对于金融资管债权而言,由于金融资管产品多数是依赖于资产管理合同构建的“信托关系”,资管产品本身也具有明确的存续期限,而且考虑到金融资管产品投资收益率的因素,多数金融资管产品合同也会将“债务人破产或进入破产程序(破产重整程序)”等类似情形作为金融资管产品终止或解除的触发条件。
在此背景下,当债务人进入破产,特别是破产重整程序时,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合同(委托人与受托人)、债权合同(受托人代表资管管理合同与债务人)所构建的双层法律结构,就可能会直接转换为资管管理合同委托人(受益人,通常为同一法律主体)、资产管理合同受托人(代表资产管理产品)以及债务人的三方关系,从而使得破产重整方案的制定、破产重整程序的推进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因此,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有必要针对金融资管债权的特性,对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认定与应对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进行必要的研究分析并作出恰当应对,以更好推动破产重整程序的实施。
一、破产重整中的金融资产管债权的认定与应对
金融资管债权,顾名思义,是指以金融资管产品为主体进行各类债权投资所形成的债权。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为委托人利益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或外币形式的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资金信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等。”
在实务中,对于金融资管产品直接以借款或其他债权投资方式与债务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认定与确认上相对容易。然而由于金融资管业务受分业监管框架的影响,特别是在《资管新规》出台前,不同监管条线下的监管要求与操作尺度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部分金融资管产品通过叠床架屋、多层嵌套等方式进行监管套利,此外金融资管产品与债务人之间构建的交易结构也非以“借贷”方式或债权投资方式出现,从而增加对于此类非典型债权的认定与识别难度。
1.“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交易的认定”
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交易为例,“收益权”本身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无明确定位,法律性质亦无明确界定,尤其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并没有收益权的表述。在司法文件层面,仅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出质的,按照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处理。【2】
在实践层面,“收益权”最先是作为一种被认可的金融产品出现的。如2013年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2016年4月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6】82号)等,都对金融机构收益权交易作出了规定。尽管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并没有关于“收益权”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大量以各类收益权作为金融产品的争议纠纷的出现,客观上推动了司法层面对于收益权性质及效力的认可与处理。
例如,南昌市高院在《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一案中首先确认收益权的债权属性。南昌市高院在判决中确认【3】,“从内容上看,本案的’资管计划收益权’应属于特定资产收益权的一种,是指交易主体以基础权利或资产为基础,通过合同约定创设的一项财产性权利。从法律性质上分析,我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明确采纳了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定原则包括物权客体法定)。因此,作为约定权利的特定资产收益权不宜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核心在于收益,通常不具有人身色彩,而具有比较明显的财产权利属性,依法可以作为交易客体。债券本身含有包括收益权在内的多项权能,权利人可以将其中的一项或多项权能转让给他人行使,而收益权作为一种债权属性,在转让行为之性质与资产转让存在根本差异。故特定资产收益权应定性为债权性质,其处置应当参考债权转让的相关原理,不宜直接按照物权方式进行处置。”
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并吸收了江西高院有关“特定资产收益权”的裁判思路,在上述案件的二审判决【4】中对于“收益权”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与辨析。最高院首先对收益权进行了区分,其一是有特别法律认可的收益权,此类收益权包括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在司法层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或政策文件将此类收益权作为准物权予以认可。该规定将部分不动产收益权纳入《担保法》“权利质押”范围。但是收益权的法律性质在无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其权利属性进行分析。对于物权,权能与权利相分离极为常见,所有权人可以将所有权中的部分权能与所有权本身相分离而单独转让给其他人,在其物上设立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以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而债权虽为相对权,但其内部亦存在多项权能可以明确分辨,这就为其权能与权利的分离提供了基础。除了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我国法律对其他财产性权利并未禁止。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底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89条明确“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特定资产或者特定资产收益权,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如果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无条件回购的,无论转让方所转让的标的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交付或者过户,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对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定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民法典》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在一定期间后再由债务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回购,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回购义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第二款规定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使得此种交易模式的认定与处理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2.“明股实债”交易的认定
“明股实债”(或“名股实债”)同样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实务中通常是指“投资方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入目标公司,通过约定刚性兑付条款实现退出,取得固定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
当前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名股实债”概念并未作出明确的法规规定,可资借鉴的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2017年2月13日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5】,该规范注释3对名股实债进行了详细定义:“本规范所称名股实债,是指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资方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方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者偿还本息的投资方式,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赌、定期分红等。”
在实务层面,有关“明股实债”的认定处理,常常会与“附回购条款的股权投资”、“让与担保的债权投资”等概念夹杂混淆,存在辨析与认定的困难和争议。特别是在目标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对于“明股实债”交易性质的认定就直接影响了相对方的身份以及参与破产程序的权利义务。如果“明股实债”被认定为股权投资,则投资方不构成债权人,无法以债权人身份参与破产重整,而“明股实债”被认定为债权投资或“让与担保型债权投资”,则其当然有权债权人身份参与破产重整程序,其投资款亦应认定为“债权”。
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明股实债”性质认定,不仅考察交易结构的设计与安排,还需要根据交易的实际履行情况予以厘清判定,例如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武汉缤购城置业公司与国通信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法院在判决书【6】中认定:“该笔款项虽系基于涉案《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但对于款项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协议名称进行判断,应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真实目的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首先,根据《增资协议》第7.1条、第7.2条、第7.3条等条款的约定,本案中,国通公司签订上述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向缤购城公司融通资金而收取相对固定的资金收益,这与一般意义上为获取具有或然性的长期股权收益而实施的增资入股行为并不相同。……其次,国通公司虽经工商变更登记为缤购城公司股东,但缤购城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国通公司实际参与了缤购城公司的后续经营管理……再次,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缤购城公司不仅在涉案《债权确认协议》中认可“国通公司依据《增资协议》对缤购城公司享有的金额至少为11408.25万元的债权”,且在(2016)鄂01民初5905号案件庭审中也认可“增资扩股争议的标的额11258.25万元加上150万元全部汇入了公司。目前我们增资扩股争议的标的额全部通过还款形式还给国通公司”“确认实际上属于名股实债的关系“……”
在上述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争议款项性质的认定,并没有仅依据协议名称进行判断,而是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真实目的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而在另一件涉及破产清算的案件中,主审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明股实债”交易结构的认定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区分,法院认定【7】:“……本案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纠纷或股权转让纠纷,而是港城置业破产清算案中衍生的诉讼,本案的处理结果涉及港城置业破产清算案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应适用公司的外观主义原则。即港城置业所有债权人实际(相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而言)均系第三人,对港城置业公司的股东名册记载、管理机关登记所公示的内容,即新华信托为持有港城置业80%股份的股东身份,港城置业之外的第三人有合理信赖的理由。……如果新华信托本意是向港城置业出借款项的,港城置业从股东会决议来看亦是有向新华信托借款意向的,双方完全可以达成借款合同,并为确保借款的安全性,新华信托可以要求依法办理股权质押、土地使用权抵押、股东提供担保等法律规定的担保手续。如原告在凯旋国际项目上不能进行信托融资的,则应依照规定停止融资行为。新华信托作为一个有资质的信托投资机构,应对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晰的认识,故新华信托提出的“名股实债”、“让与担保”等主张,与本案事实并不相符,其要求在破产程序中获得债权人资格并行使相关优先权利并无现行法上的依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客观来说,对于“明股实债”是否构成“让与担保型”债权,因《民法典》生效前的《担保法》、《物权法》均未有所规定或涉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明股实债”构成“让与担保”债权,在认定和处理上相对谨慎。针对实践层面的这一现实问题,《九民纪要》首先认可了非典型担保的法律效力。其第66条规定:“当事人订立的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虽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是其担保功能应予肯定。《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最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认了“让与担保”的法律效果【8】,使得“让与担保”的认定与处理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如上所言,对于涉及“明股实债”结构的交易,破产管理人在对其是否构成“债权”认定时,应当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考察协议签署的背景、具体的设计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区分是正常的股权投资,还是追求固定回报的债权投资。在案情复杂难以认定时,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确认。
注释
【1】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融资”模式的检讨与改进路径》,载《证券市场导论》2010年第3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20年12年31日废止。
【3】(2015)赣民二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808e45dfe8964cf6b55b21025cb7a312,最后访问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
【4】[(2016)最高法民终215号]民事判决书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74f14f092104418db94da99900a772bc,,最后访问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
【5】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zcgl/zlgz_zcgl_zhl/201912/t20191222_7648.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
【6】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32号)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e4123123173c4dfa9fb8ab470124e9ff,最后访问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
【7】民事判决书((2016)浙0502民初1671号)https://www.itslaw.com/detail?initialization=%7B"category"%3A"CASE"%2C"id"%3A"2a147749-cc46-4c6d-8a78-99abdcb7b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三十五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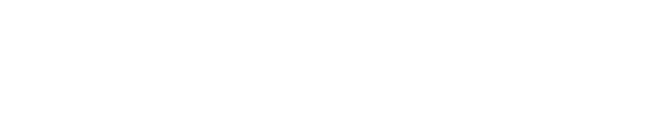
.png)
.png)
.png)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