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宇婷
【摘要】
“无损害”规则作为英国普通法下一项民事诉讼特权渊源流长,该特权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被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对“无损害”规则介绍以及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分析,为从事相关涉外业务的人员提供参考。
一、“无损害”规则概述
“无损害”规则,英文表述为“Without Prejudice”或“Rule of Without Prejudice”。也有部分中文著作将其翻译为“不损害固有权利规则”[1]。他是指“不影响实体权利”,即当事人的法律权利或特权未受损害或丧失。
该规则早期萌芽于18世纪的英格兰,以仲裁为首的有别于法院庭审的争端解决方式逐渐兴起,起初当事人双方与庭审相关的基于争端解决达成的协定并不被法庭所认可。最早在Baker v. Paine案中,Lord Hardwicke L.G. 法官认可了庭前协议作为证据的效力[2],但该案中对于庭前协议只用于证明要约人对双方合同理解模糊之处或者要约人对有约束力的商事交易习惯的认知。法庭并不认可庭前协议的强制效力。上述适用亦不因当事双方在协商过程中是否使用“without Prejudice”术语而受影响。
到了1760年至1820年,从Lord Mansfield法官开始,允许“一个人不因‘息事宁人’的行为而处于不利”,Lord Kenyon C.J. 法官将该原则适用到了数个案件当中,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下三个规则:1.基于争端解决,一方当事人因“息事宁人”而达成却未实施的协议,不应成为呈堂供证;2.上述协议与协商并不构成承认,应从证据中排除。3.法庭愈加关注息事宁人的协定与承认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未达成的协议中作出的承认保护范围 。Lord Kenyon主办的几个案件当中,在争端解决协商过程中附带的承认是被法庭认可的,与此同时,在争端协商过程中被承认的事实也是被法庭认可的。
1822年到1830年间的四个判例使得“without prejudice”书面用语变得普遍。该用语被律师明确提出以此区分被代理人因为息事宁人而作出的妥协和对承担责任的承认。到1830年,Lord Tenterden C.J. 法官在Wallace v. Small案中提出:“并非是没有损害,任何值得信任的妥协邀约都应良好的作出且没有任何限制”“without prejudice”是一个“区分标志”。此后案件少有涉及是否含有“without prejudice”术语的争议,人们转而关注协商中对“无损害”适用的范围的界定。
到了1850年,随着“without prejudice”术语被大量应用,人们的关心从它是否作为争议解决中可以被排除的证据转变成了该术语精准的含义。在Woodard v. The Eastern Counties London Blackwell Ry. Co., 一案中该术语变得明确。Wood V. -G. 在该案中说道:“‘无损害’术语并非指一方不受协商约定的约束,而是整个协商作为一个友好条约,不应构成对任何一方的损害”[3]。
截至19世纪末期,遵循先例的原则使得人们通过寻找各方真实意图的方式解读和划定“无损害”规则的范围。Lindley L.J. 法官在Walker v. Wilsher案的裁判中对“without prejudice”作出了被引用最多的经典解释:“‘无损害’到底有何含义?我认为这意味着写下邀约的一方不因他提出的条款不被接受而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写下的条款被接受且合同成立,尽管表达了无损害,实际已经修改了之前旧的规定而成立了一个新的约定”。
“无损害”规则在采用英美法系作为司法体系的国家已经成为诉讼中证据规则的一部分。该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在和解谈判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畅所欲言进行谈判,而不必顾虑对方会拿谈判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在以后的诉讼或者仲裁中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明[4]。目前,因为普通法系在全球的推广而被广泛适用。
二、国际商事仲裁中普通法系的影响
国际仲裁区别于国内仲裁的主要特征就是仲裁程序的参与人,包括当事人、代理人与仲裁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存在法律文化的差异。仲裁员对证据事项的处理或多或少的受到其所在的法律背景影响。
国际商事仲裁的“美国化”这种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它是指普通法国家,尤其是美国诉讼中的一些做法,比如高成本的审前证据开示,高度对抗的交叉询问,对证据出示提出异议等对国际商事仲裁产生的影响[5]。
国际商会的刊物Chambers Global评选的“全球最佳律师”显示,注重个人魅力传统的法国律师事务所,已经不敌高度组织化、团队化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上,普通法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占据了明显优势。排名前八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七个是普通法系的。一份在美国律师中所做的调查显示,在欧洲的仲裁机构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四十宗仲裁案中,虽然每宗案件至少有一方为欧洲的当事人,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当事人都会选择美国的律所为他们代理。
同时,从法律执业教育方面看,全球范围内年轻而有抱负的律师觉察到了这一趋势,他们成群地涌向美国法学院通过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借以“乘风破浪”,并且以在美国律所工作的经历为炫耀的资本。在这些法学院,大批的非美国人加入了建立在美国法律及其法律文化基础之上的律所,他们的事业因此走上捷径[6],这也是大陆法国家无法相比的。
此外,英语已经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最常用甚或是唯一通用的语言。普通法系的律所和英语是出双入对的,它们互为共生体: 前者的壮大促使了后者对仲裁的支配,而且这种支配也促使更多的委托人寻找普通法系的律师作代理人。
迄今为止,那些受过英文法律职业培训和那些有罗马法教育传统的人之间针对诸如“国际商事仲裁如何运作”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持续争论。但基本没有争议的是,国际商事仲裁界在全球形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圈子,其成员的经验日益反映出普通法系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历史传统、学术及实践训练、机构之间的关联,还是客户基础趋同等方面的原因所导致[7]。普通法法律文化的这种强势地位,必然会对仲裁程序产生影响。
三、意思自治及仲裁证据规则的适用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个人福利之最大化是一切法律活动之原动力与归宿。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具体到仲裁程序来讲,除特殊情况外,当事人可以决定仲裁程序中的所有事项,包括仲裁庭的组成、仲裁进行的规则、证据规则、裁决作出的方式等[8]。当事人和仲裁庭在确定仲裁程序规则方面的分工是,当事人从整体上确定程序,而仲裁员则有权利决定最终程序的进行及程序性事项[9]。
大多证据事项属于程序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也有个别证据问题的性质仍然存在争议。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的法律适用是区别对待的,两者未必指向同一法律[10]。证据问题的识别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适用,因此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仲裁庭错误地适用证据事项的法律,并违反了仲裁程序准据法的规定,仲裁裁决可能被撤销或被拒绝执行[11]。如果证据的法律适用违反了实体争议的准据法,这将通常不会影响裁决的效力,因为各国法院通常不审查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实体问题。
在此,仲裁程序准据法的确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仲裁法本身就包含了一些与证据相关的规则,是仲裁证据规则的一个渊源;同时它对程序自治包括具体仲裁证据规则的确定与适用会产生影响。早些年间,关于仲裁程序法的选择与适用,存在着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争,在1985年出台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条第2款采纳了客观标准,此后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应由仲裁地的法律管辖成为业界共识。
作为业界权威的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之一,《2021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202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于2021年5月6日正式发布。根据该报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以下简称“ICC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简称“SIAC”仲裁院)、中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简称“HKIAC”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中心(简称“LIAC”仲裁院)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五大仲裁机构。
上述五个中心其中三个均属于普通法系司法地区或国家。因此“无损害”规则在适用普通法证据规则的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会被广泛适用。
四、后疫情时代ADR的兴起以及“无损害”规则的适用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可翻译为纠纷之非诉讼解决,原意为人们试图建立不以国家公权力裁判解决争端的方法[12]。该制度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正处于“诉讼爆炸”阶段,法院积案严重、诉讼费用高昂、审判程序迟延。司法危机迫使人们另寻出路,各种便捷快速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
最早采用ADR的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法院,他们的做法大致是:一定诉讼标的额以下的民事案件一律须经附设在法院的仲裁程序,仲裁员由律师和退休法官出任;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结论无异议,仲裁裁决立即产生于法院判决同等效力,案件宣告终结;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无效,随之转入普通诉讼程序[13]。由于ADR的诸多优点,众多商人、社团和公司企业纷纷转向ADR,寻求非诉讼处理程序。鉴于ADR取得的显著成效,1983年美国联邦法院决定:如果当事人对能否由仲裁解决争议存在分歧,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继联邦法院作出该决定后,美国法院附设的ADR便迅速增加,各州亦纷纷通过立法推动ADR的发展。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美国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ADR。
在美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都在建立与本土国情相符的ADR制度,ADR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因为他不仅能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最根本的是他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以及实现多向度的调解功能。
2020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国际商事纠纷数量也因为疫情原因有所增加。然而根据各国政府基于疫情防控采取的隔离措施使得线下庭审变得困难。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困境,采用新型技术和设施实现远程聆讯、增加庭前ADR的协商是民事司法领域重大变革。
根据《2021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59%的跨国争议会选择通过ADR结合国际商事仲裁的方式解决,31%选择国际商事仲裁解决,6%选择通过ADR结合跨国诉讼解决。由此可见,ADR作为跨国争议解决在后疫情时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若是涉及跨国争议的双方在经历调解、斡旋、调停等ADR争端解决机制后并未达成一致,而后该争议被诉诸国际商事仲裁,则极有可能被由普通法系背景组成的仲裁庭、律师适用“without prejudice”规则,在ADR程序中涉及争议解决的内容被仲裁庭从证据中排除适用。
五、结语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和解谈判是非常正常的程序。在日益增加的国际商事争端磋商当中,在大量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法律文件、往来函件中无疑会涉及到履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普通法背景的当事人或其代理人(通常是律师)多数会利用“无损害”规则,事先就将包含有可能对其不利内容的文件排除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或仲裁的证据采信范围之外。导致中方无法援引相应的文件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仲裁中处于被动。因此,对于经营涉外业务的中国企业、办理涉外业务的律师都有必要了解、掌握“无损害”规则,以便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掌握主动权,保护中方当事人应有的利益。
注释
【1】刘超《浅析英国证据法中的“无损害”规则》
【2】David Vaver, Without Prejudice Communications--Their Admissibility and Effect, P4
【3】Wood V.-C. said: The correspondence was to be 'without prejudice'; which means, not that the parties are not to be bound by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course of that correspondence, but only that the whole is to be considered as an amicable treaty, not to be strictly construed to the injury of any party. When a party has exhibited what he considers reasonable terms on a treaty 'without prejudice', his course is quite evident, and why he adopts it. It is as if he were to say. 'I send you a proposal, and expect your answer, and shall make use of your answer with a view to Costs.'
David Vaver,Without Prejudice Communications--Their Admissibility and Effect, P8
【4】赵宗钰《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披露中的特权问题》
【5】崔起凡《论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规则的确定与适用》
【6】Roger Paul Alford 《The American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Vol.19, 2003, P80-83
【7】陈东《跨国经济法的“美国化”及其本质》
【8】顾燕《论法律文化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影响》
【9】Julian D.M. Lew QC, Loukas A Mistelis, Stefan M. Kroll,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P522
【10】艾伦.雷德芬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11】参加《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d项,《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4条第2款、第36条第1款
【1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版 P3
【13】乔钢梁《美国法律的调解和仲裁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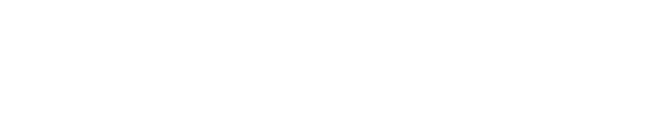
.png)
.png)
.png)
.png)


